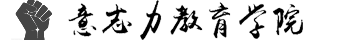来源:中国中小学教育网 作者:佚名
减弱刺激
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,席德斯的试验中就使用了阈下刺激:尽管受试者无法察觉刺激,却能据此改变自己的回答,因此刺激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。这样的试验想要证明的是知觉不一定需要意识参与。这里最常用的一种策略就是减弱刺激,其中包括减弱对比度(减少刺激和背景之间的差异),或减少刺激在屏幕上展示的时间(只展示几毫秒),或让它(以很小的时间间隔)在另一个“掩蔽刺激”之前或之后出现,例如马赛尔的试验。
还有其他的掩蔽技巧,包括在呈现刺激的同时呈现干扰刺激,甚至对一只眼睛展示色彩多样、十分鲜艳的动态图像,而对另一只眼睛展示目标刺激。与其他刺激方法不同,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使遮蔽时间长达几秒钟。
这类研究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,即强度和有效程度之间的矛盾:如何确保刺激弱得无法进入意识,又强得足以影响行为?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明确的答案。
为了探索不借助遮蔽而达成阈下刺激的方法,我们最近在比利时自由大学开发了一种设备,能够在屏幕上展示最短只有20毫秒的视觉刺激。这一设备能够让图像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屏幕上闪现,不需要任何遮蔽,受试者也不会意识到图像的出现。那么,如果将这种图像用于启动效应试验,我们会发现什么呢?
初步试验结果显示,在这样的条件下,只有当刺激可见时,它才会对行为造成影响。只有当受试者报告察觉了刺激,我们才会观察到启动效应。令人惊讶的是,从无法感知到能够感知之间,时间的差异极小:当图像展示175毫秒时,受试者看不到图像,也不会产生启动效应;当图像展示350毫秒时,受试者报告看见了图像,我们也能观察到启动效应。这或许表明遮蔽的作用原理主要是改变注意力,而不是通过对比让刺激减弱。
第二种策略是通过转移受试者的注意力,让一个刺激变得不可见。我们知道,有意识的感知有时候取决于刺激的质量(如持续时间、对比度),以及我们在一个情境下的注意力。“变化盲视”现象(对电影中的场景添加一个物体,我们会无法察觉)就很好地解释了注意力在意识处理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
1999年,美国科学家丹尼尔·西蒙斯(Daniel Simons)和克里斯托弗·查布里斯(Christopher Chabris)进行了一项著名的试验。他们让受试者观看一部短片,内容是两个三人小组在狭小的空间内互相传球,一组队员身穿黑色球衣,另一组身穿白色球衣。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计数,看看穿着白衣服的队员进行了多少次传球。受试者们不知道,第七个演员穿着戏服扮成大猩猩的样子,从右侧缓缓走进镜头,并且在场地中央停下来,拍打自己的胸脯,然后从左侧离开。只有寥寥几个受试者报告看到了不寻常的镜头,这令所有人大吃一惊。而且,如果让他们重新观看短片,不计算传球次数,所有人都能马上发现那个闯入者!这个“看不见的大猩猩”试验的各种版本如今已经在全世界广为流传,告诉我们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是不完备的,而且我们很难承认这一点。
通过其他方式让一个刺激消失也是有可能的,例如注意瞬脱:要求受试者在一系列的刺激物(每秒6到29个物体)中识别出两个特定的刺激物,它们与其他刺激物的颜色或性质不同,从而直接操纵受试者的注意力。当这两个目标物出现的时间间隔足够短暂(相差几百毫秒),受试者就不会意识到第二个目标。
这些研究面临着另一个两难的问题:只有当受试者的体验结束之后,观察者才能提问。提问的过程本来就会马上吸引受试者的吸引力,使其转向我们所寻找的、本该处在意识之外的东西。
第三种策略更加微妙,它对情境进行了描述,让受试者对情境的感知与现实并不相符。这样的案例包括安慰剂效应、暗示,甚至催眠,这些方法都能影响受试者对事物的感知。
2016年,在法国图卢兹脑与认知研究中心,安德里亚·阿拉米亚(Andrea Alamia)和同事们就在一系列试验中采用了这样的策略,他们证明了确实存在无意识学习现象。研究人员让受试者观看一团由点构成的云,点朝各个方向运动,受试者需要判断大部分的点运动方向是向左还是向右。经过若干次尝试之后,这些点被涂上同一种颜色(绿色、红色或蓝色),受试者有时需要回忆它们是什么颜色。受试者所忽略的一个信息,就是这三种颜色中有两种与点的运动方向相关,他们可以据此回答问题,而第三种颜色与运动方向无关。因此,尽管用其他方法来完成任务都会十分困难,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观察颜色,这能大幅改善受试者的表现。
在试验过程中,没有一个受试者报告发现了颜色和答案之间的关系,但是试验结果表明他们全都(无意识地)逐渐注意到了。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关联,或许是因为颜色的出现被研究人员描述得就像另一个点,与其他的点之间没有任何关联。
在简单回顾了所有策略之后,我们能总结出什么?对于从阈下感知到无意识学习的各种潜意识认知现象,我们有两种可能的态度。首先,我们可以全盘否认这些现象,认为我们精神生活的全部都必须是有意识的。尽管这种观点看起来没什么说服力,一些研究人员却大力捍卫它,不仅毫无理由地批评方法论中的诸多不确定性,称它持续污染着这个领域,还将所观察到的结果归因于使用的测试方法不够灵敏,或受到了没有被充分控制的变量的干扰。尽管大脑确实能够在意识不参与的情况下处理信息,例如盲视现象所证明的那样,但是这些能力的存在无法证明存在一个强大的潜意识认知。或者说,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能力并非来自于意识,而是来自于一些简单的神经功能,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自发的。
另一种态度就是承认某些信息能够在意识不参与的情况下得到处理,例如语义信息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决,这种潜意识认知的界限究竟在哪里?根据现有的研究证据,我们能够肯定地回答,尽管这些无意识处理过程确实存在,但它们都是短暂的、表面的,通常不会对行为造成影响。所以,没什么理由担心我们有可能被操纵,因为相比操纵我们的潜意识,通过劝说或建议的方式直接影响意识要容易得多。如果确实存在那样一座冰山,那么浸没在水下的部分就是意识的神经基础,而非我们的心智中某个隐藏的部分。
要想将这个辩论再推进一步,一种方式就是假设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边界是流动的,它很容易受学习过程的影响而发生大幅度的改变,并且在一生中都具备弹性。
流动的边界
我们以驾驶汽车为例来解释。在车子启动阶段需要有意的控制,需要意识的介入,但这一过程逐渐被一系列的自发行为所取代。自发的驾驶十分流畅,一个熟练的驾驶员能够毫无困难地一边驱车行驶在道路上,一边和身边的乘客聊天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意识不完全是缺失的,更像是可选择的。但是这种情况与阈下感知十分不同,它促使我们反思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,即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,我们对世界的有意识感知是一个动态过程。这有点像一条河流,随着时间的推移,河水的流动也在塑造着河床;自发的信息处理也是一样,它既发生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,又改变着我们的精神世界。
要想辩论更有意义或许还需要持续发展技术,将大脑过程可视化、量化。今天的大脑成像技术,尤其是某些分析方法,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码大脑活动,为探索无意识和意识处理过程之间的关系提供美妙的可能。
2018年,在日本京都的国际先进通讯技术研究所,文森特·塔斯切罗-杜姆切尔(Vincent Taschereau-Dumouchel)和同事们证明,只要记录患有蜘蛛恐惧症的人的大脑活动,同时要求他们尝试通过思想控制屏幕上一个圆圈的大小,就能减轻焦虑。受试者们没有注意到,圆圈的大小是随算法控制而变化的。算法实时追踪他们大脑中的活动,观察一个与蜘蛛相关的神经通路的活动变化。换言之,通过这种神经追踪方法,我们能够通过抽象图像有意控制潜意识活动。这样的方法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潜意识,同时更深入地了解意识本身的机制。
文章选自《环球科学》杂志2019年第11期。
·上一篇文章:新冠肺炎疫情2020延迟开学不是延时学习,停课不是用来休息是用来反超的
·下一篇文章:无
转载请注明转载网址:
http://www.yzljy.cn/news/jybkzs/21121115610I540J6FHCJ301F88K4AJ.htm